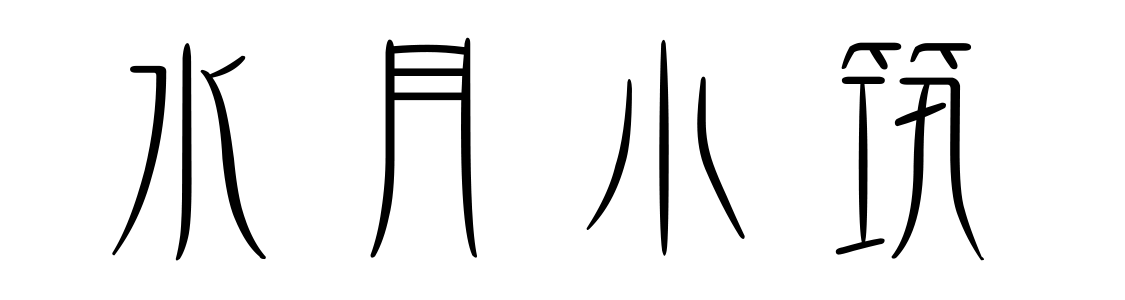你和陌生人有过哪些有趣的互动?
我和陌生人在油菜地里发生过枪战。
这个能算互动吧。
倘若算的话,那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了。
一八年年末,我当时提前一个人回了老家,一边先打扫卫生准备过年,一边偷点清闲。众所周知,当父母完全没有打牌以及购物等爱好的时候,他们就会把多余的精力全部释放在你身上。
就好比我爸妈,他们那都不能叫释放了,简直叫开闸。
所以我独自跑回老家,耳根子还能清净点。
那时候我突发奇想,想在院子里头的水缸养黄鳝,于是当天下午我就提着篮子,锄头,上山挖泥巴去了。
就在油菜地,我趴下来就是一顿挖,然后还挖出了个袜子出来。是不是很离奇,诸位,直至我现在动笔写下这个回答的时候,我依旧还是不知道,为啥我会从油菜地里挖出个黑袜子。
还很小,应该是个小孩子穿的,因为当时我穿了下,套不进去。
偏题了偏题了,总之就是当时我挖的正起劲,忽然就感受到了一股杀气。
我没开玩笑,请相信我这样敏锐的人类对于处境变化的判断,因为当时我一直听到有人在喊biubiubiu。
有人在枪击我。
我赶忙起身回头,发现是一个中年男的缩在油菜后头,用一只手做出枪的形状,正对着我射击到忘乎所以。
说实话,我一看他就知道是个精神病,真的。
这倒不是指他这么大年纪还脏兮兮的,并且穿个小号的学生校服,而是农村很多这种精神病患者,他们都红光焕发的。
我也很纳闷儿,这是啥传统吗。
不过这也不重要,因为我当即就愤怒了起来。大家伙儿都是精神病,我他妈还能把你给惯着了不成,我立马就把锄头丢了,然后双手并用,一前一后。
我这个叫步枪,所以可以喊哒哒哒,比他打的快。
他肯定打不过我,而且嘴皮子也没有我快,于是在躲闪了两下后,他就开始向后跑,紧接着我便端着手追了过去,不停地冲着他哒哒哒。
我就这样追了他半个山,在油菜田里跑到看不清影子。
但很显然,他不是我的对手。
因为没多久他便实在跑不动了,就直接躺在人家地里头,不停地说,你把我打死了,你把我打死了,你手枪打的太快了。
我寻思他是不是有病啊,我这明明是步枪。
不过这也不重要,因为接下来我便把他拉到田埂上去坐着,田埂上种着桑树,很矮,坐两个屁股墩儿没问题。
说实话我也跑累了,于是摸出根烟点上,我本想给他也点一根,但想到他那最多八岁的智商,还是收了回去。
可这傻子忽然就打断我了,他让我给他拿一根儿,我说你不会抽,他非得说他会。
好吧,正常人不能跟傻子计较,我便把玉溪分了他一根。
他确实抽了,只不过没点燃。
真精神病啊我靠。
你是谁啊,傻子忽然问我,我低着头抽烟,顺口就甩给他一句,我是你爹。
“爹”
好吧,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叫爹,对方大概率还是个年过四十的中年精神病。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,但我确实被逗笑了,这使得我愿意坐在那儿再和他扯几句。
就在这有一搭没一搭的对话里,我也差不多摸清了他的情况。
我估计诸位看到这里会好奇为啥不把对话也写下来,那是因为这对话实在是支离破碎,废话连篇,而且还伴随着大量的心理活动。
可作为读者,是绝不可能从我的文字里感受到我的斤两,我的玉溪,以及我的屁股当时坐的痒不痒。
所以我觉得这没意思,干脆跳过。
总之吧,这傻子就在隔壁大队,转过山腰多走两步就到了,他还问了我住哪儿,我随手便指了指山底下的房子。我当时还在想,这怎么得也算是个暴力分子,怎么还给放出来了呢。
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做的不到位啊,点评批评俺们村儿。
之后通过艰难的对话我才晓得,原来他家里只有他和他妈,而她这两天已经躺在床上起不来了。
你咋吃饭呢?我疑惑地问他。
傻子想了想,跟我说他就吃的屋里头放着的红苕,生的,他还给他妈喂过,但他妈没有吃。
我心想着这不废话吗,你妈要还能生吃那玩意儿,你们家除了精神病又得出个变异人了。
把烟头扔地上,我有些唏嘘地跟傻子说,那你快死了。傻子说我在放屁,他不会死的,他还要去看珠穆朗玛峰。
我有些乐呵呵地问他为啥是珠穆朗玛峰,他说他妈说过山上有神仙,珠穆朗玛峰就是他晓得的最高的山,所以他要去山上找神仙救他妈。
说完他便接着抽那根压根儿没有点燃的烟,腮帮子不停地胀大缩小。
我低下头折断了一根干瘪的树枝,我想这傻子真是傻子,他不知道我说的是真的,他真的就要死了,等他妈死了以后,他就会死,因为不会有人管他的。
起码我知道,大山里真的不会有人管他的。
见我不说话,这傻子又说话了,他非得问我见过珠穆朗玛峰没有,我说我见过,然后便给他描绘了一下那山有多高,有多大,山上住着多少神仙,有叫耶和华的,还有叫玉皇大帝的。
他越听越兴奋,连带着眼睛里的明亮也愈发散开。他说他肯定要去,让我以后带他去,他喊我叫爹,给我拿红苕吃。
我点了点头,那天的谈话也就到那儿为止了。
当天晚上是我这辈子睡得最不舒服的一次,因为我始终睡不着,我在想我要不要把屋里头的腊排骨,香肠,拿一点到他们屋头去,我想我大概能够知道他房子在哪儿。
但我又在想这关我什么事呢,那是个精神病,谁知道说的真的假的。而且我疯了,我非要莫名其妙跑这一趟,难道他多吃几顿饱饭就不会死了。
他肯定会死的,只不过会死在他妈后面,再说了我又不是没有见过死人。
可我就是睡不着,我就是闭上眼睛就会想到他缩在屋里头吃红苕,然后给他妈不停地喂。
我觉得好荒唐,我这样的人,我为什么会产生类似于怜悯的情绪。以至于那天晚上我还看到了荒诞的画面,譬如看到他在窗子外面比着手枪的姿势,在油菜地里跑。
我有些浑噩了,不知道那到底是幻觉还是真的。
第二天我也没有去,但他也再未出现在我家附近,我也没有散步往他家的方向去过。
说来很奇怪,就隔了个山,但再也没见过。
我上述所讲的一切,竟然就是唯一一次见面。
好像一瞬间土地丈量的尺度都宽阔了起来,遥遥远远的油菜田里,能把人困住一辈子出不去。
我过完年就走了,再回来时已是第二年的年末。
问过我幺爷,果然傻子已经死了。
他还真过来给我送了两个红苕,就放在院子里那个洗衣台下面,就俩他还怕人给偷了。
他妈死的很快,之后他自己又活了段时间,然后在外头水塘被淹死了。果然傻子就要有傻子的死法,这就是人的命。
人哪儿能改变的了自己的命啊。
我听幺爷的,在山脚底下左拐右拐,然后找到了他的坟,应该是村里人给他堆的,紧挨着他妈。
就一土包,我连他名儿叫啥都不晓得,不过这太正常了,因为我也同样不知道他的人生,他的过去,乃至于他为什么会得病,但那关我什么事呢,一点意义都没有。
这些都属于他自己,现在又藏在坟里。
我想傻子嘛,死的太清太浅,以至于他的死都不会留下什么痕迹,一下子就幻灭掉了。
像盆子里的纸灰一样,吹一下就飞老远,落在地上看都看不见。
我点了根烟,然后拿手在地上刨土,在他的坟前又给他堆了一个小土包。
我说,这就是珠穆朗玛峰,它其实就是这么个玩意儿,你自个儿在坟里慢慢看吧。奇了怪了,大家伙儿都是精神病,怎么你全说的真话,我全说的假话呢。
你真不是个人啊。
我也真不是个爹。
- 作者:朱慈
- 链接:https://www.zhihu.com/question/579232747/answer/2872502146
- 来源:知乎
-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。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,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。